文 /裝探員
從觀看到關照
延續關照多於觀看的工人之眼,新世代的藝術家黃榆惠(1998-)選擇進入工人父親的工地,累積數月的時間跟拍認識父親焊接鋼筋的工作。作為家人,黃榆惠自述自己不是工人也未必是在代替工人發言,僅是逼迫自己直視她曾經害怕而逃避觀看的真相——擔憂父親每天都身陷在危險的工地裡是否會發生意外,即便她三番兩次請求父親教導她焊接的工法都被父親拒絕。[1] 的確,出於愛護與期許,很少有工人會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也成為工人。正因如此,黃榆惠在集結完父親工作的攝影紀錄後,另一個系列《工.70》則轉向以負片模式拍攝,[2] 選擇還原攝影最初的印樣技術。塔伯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 1800-1877)在《自然鉛筆》(The Pencil of Nature, 1844-1946)中,提及自己曾使用投影描繪器(Camera Lucida又稱明箱)速寫眼前風景,但因為自己缺乏繪畫訓練無法達成,卻也讓他回頭思考暗箱的顯影實驗,在紙面上塗抹感光物質,直接放置採集的葉片蓋上玻璃板或是放入暗箱中曝光,形成實物因遮蔽顯影為淺色,但是背景直接受光顯影為深色的影像,也是負像或稱為負片(negative)的概念,這樣曬印的過程被塔伯特稱為光的素描(photogenic drawing)。[3] 透過光照直接得到的負片則可以藉由鹽印(salt print)的技術,再轉換為正片被複製出來,成為日後可複製出相片的攝影術起源之一。[4]《工.70》選擇返回攝影最初的負片,強化光線刻畫在父親身上經年累月的勞動痕跡。
從發展成熟的攝影術到今日數位化的攝影,雖然負片底片沖印與放大的過程不再必要,負片也轉而成為一種影像特效,喪失190年前光線落在實物上形成負像時與實物直接的接觸感。黃榆惠的《工.70》選擇使用負片的數位特效拍攝父親的肖像,影像不見主角的面容而是直視其後腦勺,頭頂有幾道深色的痕跡似乎是突起的疤痕,藏匿在髮根裡,原本的黑色髮絲轉白,而真正的白髮則如同黑色的細針,鮮明地從受光處襯托出來,使得中年的父親,透過負片的拍攝,在影像中被描繪為70歲的白髮樣貌。順著頭髮往下到頸部,皮膚一道實際上深深向內的摺痕發亮著,照見上方另一道反白的傷痕,結痂的部分則變成有如刻痕的深色疤痕【圖1】。接著,從頸部到肩部的皮膚隨著陰影逐漸變深,卻未掩蓋頸部以及皮膚曝曬過度到處突起的疙瘩。透過負片,在認知的現實與影像之間,我們必須顛倒黑白深淺的色調,重新去觀察與解讀這幅工人肖像。黃榆惠在《工.70》的自述裡引用了2017年林立青所出版《做工的人》,內容談及焊工師傅的壽命多半落在70歲,以此警醒自己去關照身為焊工的父親,[5] 她打散了不同的身體部位,有頭頂的疤痕、耳朵、臉頰、手掌、以及體毛中的疤痕,讓黑白鮮明的皮膚肌理、被放大的毛細孔紋路、交錯縱橫的體毛,皆透過負片強烈的對比刻劃出父親的身體紋路。

真實的解剖術
《工.70》的負片攝影也猶如醫療檢查詳細掃描各個身體部位的觀察方式。研究者匹克(Muriel Pic, 1974-)指出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曾將外科醫生與攝影師相提並論,比喻相機為解剖工具:「外科醫生,在一個決定的時刻,放棄了與病人這樣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位置,而是在操作上,他穿透病人的身體⋯⋯」,同樣地,由相機拍攝的影像也放棄了人與真實之間面對面的關係,因為:「影像的成功只是在於它以最為密集的方式利用機械穿透過這個真實的中心」,由機械拍攝的影像極度地人工化,甚至在現實中找尋不到,卻變得至關重要。[6] 相機的拍攝動作有如穿透人體的解剖手術,這也是為什麼班雅明要指明攝影師不只是完成工作的手術醫生,同時也是讓機械動起來的操作員,深深地穿透既有的結構,操刀去分解現實,甚至裂解社會既定的結構,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時代容顏》(Face of Our Time, 1929)的攝影中,桑德(August Sander, 1876-1964)以相機鏡頭解剖每張臉龐去發現他們的社會根源【圖2】。攝影與社會調查皆以技術取代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黃榆惠透過負片拍攝父親的身體,放大相機的解剖眼光,帶著觀者穿透過皮膚表層去揭露工人父親身上的傷痕。

然而,黃榆惠並未放棄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屬於人與人之間的關懷,修補如此冷冽陌然甚至像是醫療X光的影像。黃榆惠的《工.傷》則透過絹印重建光線曝曬的過程,再次轉印《工.70》的負片影像,將父親的身體看作是建築體,使用焊錫與鋼絲的材料直接在影像上修補與接合他身上曾經撕裂、受損的部位,以金屬材料嫁接脆弱的肉身。有時,背景猶如沾染體液的白色紗布,當焊錫材料超出了身體的部分,也成為接合與補強作品的外部材料【圖3】。另一張《工.傷》則是再次反轉負片獲得正片影像,相較於另一張負片影像的強烈對比,正片影像在黑色背景中還原出接近現實情況的側面肖像,皮膚的質感不再,轉而是模糊的身影,銀色的焊錫與鋼絲反過來融入淺色的皮膚影像裡,或者,在黑色的背景中,鑽出孔洞、拉扯出纏繞或糾結的鋼絲,以破壞影像自身的方式,讓材料被突顯出來【圖4】。

42×59.4公分。圖版來源:藝術家提供與授權。

《工.傷》中焊接與穿孔過的影像,一方面試著修補再現父親身體的影像,另一方面又戳破影像自身,暗示父親早已佈滿各種傷害的身體恐難以修補。過去的攝影以工人之眼試圖觀看工人的身體與勞動狀態,黃榆惠則進一步地回歸攝影的根源,以負片轉化攝影的拍攝過程像是外科手術,以影像照護著身為工人的父親,讓自己成為外科醫生,仔細地檢視與記錄各種潛在與顯在的傷痕,再以焊錫材料修補影像上的傷痕。這些不斷轉印的工作也使得她需要操作各種機械與材料,像是她自己的父親那樣,在工地焊接著每個建築中難以覺察的榫接點,最終成為工人攝影的攝影工人。
[1] 藝術家訪談,時間2024年1月6日,地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2] 蘇建州,〈何處安身?《像蝸牛行行走.名為家的場域—黃榆惠、謝明澄雙個展》展覽評論〉,《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ARTalks:》(2024.12.17),網址:< 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talks/524/38914>(2025年2月18日檢索)。
[3] H. Fox Talbot, The Pencil of Nature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 Longmans, 1844). “The pencil of nature,”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s, 1844 – 1846, https://digitalcollections.nypl.org/items/cff7da80-343b-0136-4130-09d7963bd8b1 (accessed Feb. 18, 2025).
[4] 相較於塔伯特的技術,1839年達蓋爾(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 1787-1851)申請專利的暗箱攝影技術則是在單一張鍍銀的銅板表面,顯影為無法複製的正像或正片。不久後,已知曉達蓋爾銀版技術的塔伯特,以碘化銀為顯影劑縮短曝光時間改良暗箱,再將形成的負片透過與相紙的接觸可以重複印出正片,進而在1841年提出卡羅版攝影術(calotype),希臘文為美麗的印刷之意。
[5] 藝術家訪談,時間2024年1月6日,地點: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6] 原出處:Walter Benjamin, “L’Œuvre d’art à l’époque de sa reproductibilité technique(1939),” Œuvres III, translate from German to French by Maurice de Gandillac, Rainer Rochlitz and Pierre Rusch (Paris: Gallimard, 2000), p. 301.
轉引自:Muriel Pic, “Leçons d’anatomie. Pour une histoire naturelle des images chez Walter Benjamin,” Images Re-vues, 2010, 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imagesrevues/409 (accessed Feb. 18, 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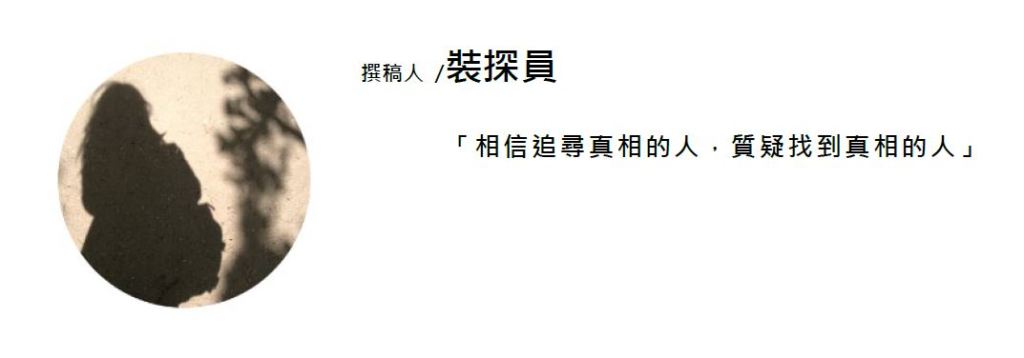





發表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