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宗文

哲學家或社會學家喜歡取藝術作品或藝術家來闡述理念。
傅科(Michel Foucault, 1926-1984)除了直接拿委拉斯奎茲(Diego Velázquez, 1599-1660)的《宮娥》(Las Meninas, 1656)【圖1】作為《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一書的引子,他也很想寫一本關於馬內(Édouard Manet, 1832-1883)的書,並且多番在演講中論及他對馬內作品的理解。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更是乾脆在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開講馬內,在1998-2000年兩年的課程中,闡述馬內本人與一系列作品承載的社會學意義。
原來,藝術作品不只是個現象,更是能以自我現身在哲學家或社會學家的工作中,以「現成物」(ready-made)的樣態來表現、介入甚至構成思想活動。從過往的哲學家工作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四種藝術介入思考的方式:
一、藝術品作為思考的現成物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在《藝術作品的本源》(Der Ursprunch des Kunstwerk, 1935)裡,藉由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的《靴子》(Shoes, 1886)【圖2】來闡述世界與大地的爭執。海德格說:「藝術作品是人人熟悉的。在公共場所、在教堂和住宅裡,我們可以見到建築作品和雕塑作品⋯⋯一幅油畫,如同梵谷那幅描繪一雙農鞋的油畫,就從一個畫展轉到另一個畫展。」[1]海德格認為這件作品為人所熟知,可以作為概念傳達上的「現成物」。於是,靴子如何透過視覺的呈現,讓來自大地的塵土,與農婦展開的生活世界,兩造連結起來。這是海德格擱置了畫家梵谷,卻讓藝術作品成為概念的工具。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在《關於歷史的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 1940)中,以克利(Paul Klee, 1879-1940)送他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 1920)來論證歷史,特別是質疑唯物的、進步的史觀何等荒謬。同樣也是讓抽象的理念,透過現成的、具體的圖像來闡述。

二、藝術家生命及其創作作為思考的現成物
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如此寫道:「從作者的一生中,我們學不到任何東西;但如果我們讀懂了他的一生,就得知了一切,因為他的一生是向作品展開的。」[2]這是《塞尚的疑惑》(La doute de Cézanne, 1948)的最後一段。梅洛龐蒂接著論道:「在世上,他仍須藉畫布、用顏色來實現他的自由。他得等待其他人的贊同,來證明他的價值。」[3]原來,當梅洛龐蒂用塞尚的作品、書信和關於他生平的一切,重新描繪出畫家一生的疑惑,塞尚堅持在自然與傳統、大地與世界、理性與感受之間的努力,也因此被認肯了。
梅洛龐蒂用塞尚活在世上的切身之苦,來闡明、讓人思考身體現象學;同樣地,布迪厄用一生飽受責難、誤解的馬內,來示範場域社會學。藝術家的「現成的」一生,是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操演思考的工具。
三、藝術家的理論作為思考的現成物
昂希(Michel Henry, 1922-2002)在1991年的一次訪談中提到:「我沈浸到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所寫的文本之中,康定斯基不僅以天才地將自己的繪畫理論化,更形成一種普遍的美學理論。」[4]他還說:「我們都根本上不屬於現代人的意識型態:我們都相信某種近乎神聖的大寫生命。」[5]這是昂希在出版《看見不可見:論康定斯基》(Voir l’invisible : sur Kandinsky, 1988)一書之後的證言。昂希這本書是基於康定斯基自己所提出的藝術理論,特別是從《點、線、面》(Point and Line to Plane, 1926)一書而來的啟發,藉由與康定斯基對話,來闡明昂希的現象學之道。
在早年,藝術家能為自己的創作理念著述者,並不多見。康定斯基有理論專書作為思想家的現成物,誠屬珍貴,但也只有昂希能夠深入剖析,相互共鳴。
四、藝術家現身參與思想建構
在《自由交流》(Libre-échange, 1994)中,社會學家布迪厄和藝術家哈克(Hans Haacke, 1936-)不僅談藝術,更談理念、談理想。布迪厄用哈克的作品和產出作品的理念來談社會學,哈克則引布迪厄的社會學概念來闡述藝術理念。原來,布迪厄對藝術界的活動並不陌生,哈克也曾使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來支援創作。
藝術家現身參與思想工作,標記著藝術家主動向思想工作出擊,而不受限於被動狀態的「現成物」。換句話說,藝術或藝術工作者,從原本在思想工作過程中的「現成」,轉而成為「現正形成」的狀態。
藝術介入思想工作的條件
上述四種模式裡的思想工作者都不是藝術家,也不是藝術史或藝術學者。他們關心的是哲學或社會學的根本問題。儘管有各種可能的介入方式,但參與思想工作過程的藝術家或藝術作品,必須是知名,或至少為人所知:入世之作才得有社會溝通的效果。這也是「現成物」的特徵。然而,即使是現成物,藝術作品的內涵或創作理念卻必須出世,要有陌生感,方能激發思考。既入世又出世,這是藝術介入思想工作的內在條件。
從內在條件衍生的另外一個條件是,這些思想家設想的交流世界,是現成物所在的世界。這是思想工作的疆界條件。讓藝術在思想中出現,原本是為便利溝通,但若讀者處在一個不熟悉藝術的社會情境,反而必須先瞭解藝術,才有辦法進入思想。例如,如果不知道誰是馬內,就進不了布迪厄的論理語境裡面,更不用說透過馬內來理解象徵革命了。文化資本的邊界效果也在這裡發生。
當界線愈加模糊
從委拉斯奎茲到哈克,雖然四種模式看來似有時序,但在它們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階段關係。然而,「在藝術終結之後」(Danto, 1998),確實思想工作的疆界已經模糊,身分不再是藝術介入思想的重要特徵。例如,在《重組現代》(Reset Modernity!, 2016)的展演中,拉圖(Bruno Latour, 1947-2022)徵召一批人參展,這些人大部分不是藝術家,卻也透過藝術形式來表現他們對「現代」的深刻質疑,繼而指向對環境生態議題的共同關懷。
換句話說,雖然思想工作的型態與藝術創作的形式之間沒有明確的階段關係,但思想與藝術仍是在歷史裡共時併進的。而且,就如我們眼前所見,當藝術不僅是思想工作的對象,藝術本身也是思想工作的過程之時,亦即,當藝術與藝術創作者不再只是思想過程中的「現成物」,更是「現正形成的」成員,而且,思想家也涉入藝術工作之時,藝術家與哲學家或社會學家的身分界線也就更加模糊了:這可以是一位從事藝術創作、涉及藝術事業的思想家,也可以是思考人間意義、創新理論的藝術家。
[1] Martin Heidegger, 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 (Frankfurt: Vittorio Klostermann, 2012), pp.3.
[2] Maurice Merleau-Ponty, La doute de Cézanne et autres textes (Paris: Gallimard, 2023), p. 46.
[3] Merleau-Ponty, La doute de Cézanne et autres textes, p. 47.
[4] 米歇爾・亨利,鄧剛譯,《走向生命的現象學:米歇爾・亨利訪談錄》(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4),頁77。
[5] 米歇爾・亨利,《走向生命的現象學:米歇爾・亨利訪談錄》,頁81。
參考文獻
Benjamin, Walter, 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 Berlin: Suhrkamp Verlag AG, 2010.
Bourdieu, Pierre, Haacke, Hans, Libre-échange. Paris: Seuil, 1993.
Bourdieu, Pierre, Manet. Paris: Seuil, 2013.
Danto, Arthur, After the End of Art.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Foucault, Michel, Les mots et les choses. Paris: Gallimard, 1990.
Foucault, Michel, La Peinture de Manet. Paris: Seuil, 2004.
Heidegger, Martin, 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 Frankfurt: Vittorio Klostermann, 2012.
Henry, Michel, Voir l’invisible: sur Kandinsky. Paris: PUF, 2014.
Kandinsky, Wassily著,余敏玲譯,《點.線.面》,新北:華滋,2013。
Latour, Bruno, Reset Modernity! Cambridge: MIT Press, 2016.
Merleau-Ponty, Maurice, La doute de Cézanne. Paris: Gallimard, 2023.
米歇爾・亨利著,鄧剛譯,《走向生命的現象學:米歇爾・亨利訪談錄》,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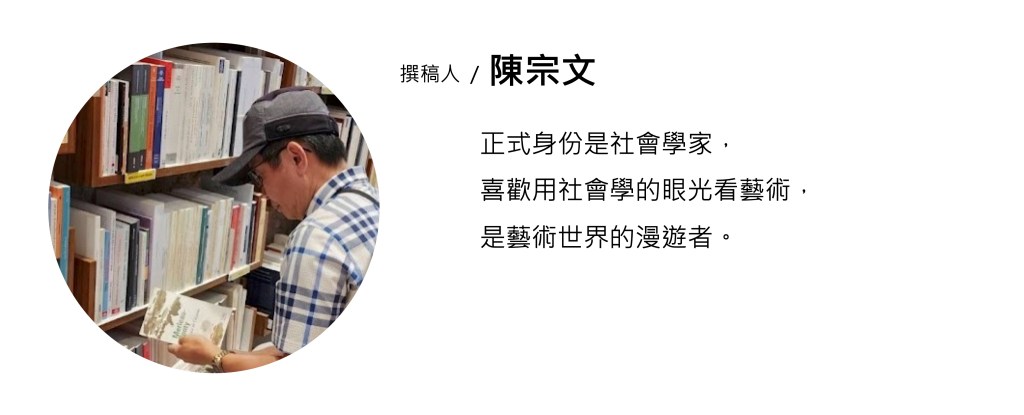





發表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