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謹為
當我們評論一幅有關動物的圖像,時常會以「逼真」、「生動」、「活靈活現」的字句形容創作者精湛的技巧;對於動物表現最高讚譽,莫過於捕捉並再現生命,召喚牠們到觀者的面前。但有趣的是,你是否想過西方傳統繪畫中動物寫實的描摹,實際上受益於對死物的觀察?反過來說,當創作者描繪的就是一幅關於動物的死亡圖像,它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又要如何觀看?
無聲無息:動物作為食物、獵物
相對於「動」物,我想先換個角度,以「靜」物來觀察動物。「靜物」(Still life)英文直譯「靜止、寂靜的生命」,其定義不外乎靜止不動、無生命物體的排列描繪。[1] 動物在靜物畫之中,常是已死的狀態,或者說以「食物」之姿現身。例如最早出現在古埃及的墓室壁畫、作為喪葬供品、象徵來世享用的佳餚。或是古羅馬別墅中的馬賽克,鳥禽、鮮魚如同肉品的代表,與蔬果同列【圖1】。[2]
直至16世紀,靜物畫於北方尼德蘭繪畫中蓬勃發展,物件除了精心擺放在打光的暗室內,更出現像阿爾岑(Pieter Aertsen, ?-1575)《神聖家庭施捨的肉攤》(A Meat Stall with the Holy Family Giving Alms, 1551)【圖2】,這類以大尺幅描繪佈滿各式肉類的市場肉舖的作品。前景動物的各種部位被切割,帶皮、帶骨、不帶臟器的,或垂掛、或盛裝,錯落鋪排成肉色的框景,透出冷色調的背景。遠方幽微地呈現新約聖經《逃往埃及》場景,聖母瑪利亞一手懷著耶穌、一手向眾人施捨。這樣世俗與宗教題材的並置,被認為是精神財富與物質利益對比的道德勸誡。[3]
同樣是大尺幅、近乎奇觀的表現形式,席得斯(Frans Snyders, 1579-1657)的畫作中是一隻隻從荒野捕來的獵物【圖3】,雖然並非都是可食的動物,如孔雀、白天鵝,但同樣以任意棄置的方式,成堆崩落到桌面底下。這些畫作由貴族大公們委託,藉由展示大量華麗巨大的動物身體,彰顯自身擁有獵場和狩獵的權力——不是因為食用而殺,而是因為「有能力」宰割。[4] 此類如同炫富競賽的靜物畫存續一個世紀之久,並由席得斯的學生揚‧菲特(Jan Fyt, 1611-1661)、揚‧韋尼克斯(Jan Weenix, 1642(?)-1719)發揮極致。

從上述的案例大致可以看出,這些動物死亡圖像的展示,往往指向動物本身之外,即來世的饗宴、精神糧食的對立面或是誇耀財富的象徵等。它,作為靜物,不只是「靜止」的物件,而是「寂靜」的軀體,難為自身說話的屍體。
聽見自然的哭喊:18世紀盧梭與自然主義
不過,有研究者嘗試為席得斯平反,Frank Palmeri就透過藝術家的交友圈,認為席得斯曾接觸並認同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和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等人反濫殺動物的思想。Palmeri更指出,席得斯的作品具有雙重語境的特質,即「它既讚美贊助者的權力和財富,又質疑殺戮所製造死亡擴散的奇觀。」[5] 確實,過去的人們面對正在死亡的獵物並非全然無感,像是蒙田〈論殘酷〉(Of Cruelty)中提到,自己雖然對捕捉到獵物感到喜悅,但卻無法直視掙扎的獵物和牠垂死的叫聲。[6]
16世紀以降,動物保護的觀念開始在思想家身上萌芽,直至18、19世紀達到高峰。啟蒙時代的哲人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可說功不可沒,其具浪漫色彩的自然主義影響後世深遠。盧梭不但認為應該如「高貴的野蠻人」回歸自然的初始狀態,也認為人與其他動物皆是「有情眾生」,當我們看見同伴或有感受之物面臨痛苦或死亡時,會自然而然地心生反感難受;基於憐憫,人們不但不應加害同類,亦不該傷害有感覺的生物。[7]
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Discourse on Inequality, 1755)甚至提出人類語言起源(在話語還不作為誘拐他人的功能之前)就是自然的哭喊聲(cry of nature),一種因為面臨危險和痛苦的呼救。[8] 或許也正因為被這種本能的「感情所困」,每當有動物遭到虐待戕害而吶喊,理性的腦袋都將為感性的聲音所震撼,如同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詩中所言:「獵兔的每一次叫喊,大腦的纖維皆會撕裂。」[9]
有聲無息:屍體為自己發聲
繼狩獵競賽之後,18世紀的英國上流社會興起另一種玩物:賽馬。人手一本韋瑟比(James Weatherby, 1733-1794)出版的《育馬大全》(General Stud Book),以蒐集純種馬血統的情報。[10] 當時不少王室貴族也委託藝術家為自家的賽馬繪製畫作【圖4】,圖像中強調馬的體格、皮毛的光澤與健康健全。
與此同時,儘管逐漸進入工業化時代,馬匹仍作為動力的生產工具,在都市和鄉村之間勞役。版畫家畢維克(Thomas Bewick, 1753-1828)的作品《等待死亡》(Waiting for Death, 1827)【圖5】,與強健碩美的賽馬圖像形成極大的反差。瘦骨嶙峋的身軀,飢寒交迫地站在傾頹的樹樁旁,絲毫感受不到活力。這樣的描繪貼近尼柯爾森(George Nicholson, 1760-1825)著作《人類對低等動物的作為》(The Conduct of Man to Inferior Animals, 1819)的描述:人們每天都可以看到年邁或肌瘦的馬匹被不良對待,最終因反覆地被鞭策,而精神崩潰、變得遲鈍麻木。[11] 這本書不僅細數人們對動物的惡行,更提倡素食主義,畢維克也為此書設計插圖【圖6】。
傑利柯(Théodore Géricault, 1791-1824)1823年《死亡之馬》(Dead Horse)【圖7】則預告著馬匹最後的景況:在一片荒地中垂死。從荒地中露出的半截車輪,暗示馬匹是被遺棄不再使用的勞動力;而遠方殘破的房舍前,依稀又有一匹馬即將倒下。

綜上所述,此時不論是垂死、將死或者精神上死亡的動物死亡圖像,皆不再是被掩飾或者僅作為他人的指涉物,而是對動物本身不平等對待的寫照。即便死亡在牠們身上逐漸蔓延,但有種聲音幽幽響起,那或許就是自然的哭喊。
小結
為了為「我們不會說話的朋友」(Our Dumb Friends)發聲,19世紀英國各式動保聯盟和期刊雜誌成立發行。[12] 例如防止虐待動物協會(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imals ; SPCA)於1824年成立,1840年代英國女王賜名並獲得贊助,是第一個長期經營且歷史最悠久的動保團體。
文章開頭,提到我們總以「栩栩如生的欺眼技巧」、「召喚動物的生命到眼前」的評述觀看動物畫。而今,我們似乎有了新的觀看方式,一種穿透寫實生動的表象下,對動物生命更真誠的看待;我們不只是看到,而是聽見自然的哭喊從繪畫平面的深處,反向我們內心召喚。
[1] Still life – Art Term | Tate: <https://www.tate.org.uk/art/art-terms/s/still-life> (Accessed Nov. 14,2021).
[2] Hans J. Van Miegroet,”Still Life,” Grove Art Online (2003): <https://reurl.cc/Ddm8X6> (Accessed Nov. 15, 2021).
[3] Ethan Matt Kavaler, “Pieter Aertsen’s Meat Stall Divers aspects of the market piece,” Nederlands Kunsthistorisch Jaarboek (NKJ) / Netherlands Yearbook for History of Art Vol. 40 (1989), pp. 68-70.
[4] Frank Palmeri, “A Profusion of Dead Animals: Autocritique in Seventeenth-Century Flemish Gamepieces,” Journal 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 Vol. 16, No. 1 (2016), p. 55.
[5]Palmeri, “A Profusion of Dead Animals: Autocritique in Seventeenth-Century Flemish Gamepieces,” pp. 61-62。
[6] Stephen F. Eisenman, The Cry of Nature (London: Reaktion Book Ltd., 2003), p. 133.
[7] 盧梭著、李常山譯,《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頁67。
[8] 同上註,頁91。
[9] William Blake,” Auguries of Innocence,” Poetry Foundation: <https://reurl.cc/e6XZOW> (Accessed Nov. 14, 2021).
[10] Eisenman, The Cry of Nature, p. 150.
[11] George Nicholson, The Conduct of Man to Inferior Animals (1819), pp. 20-21.
[12] 李鑑慧,〈挪用自然史:英國十九世紀動物保護運動與大眾自然史文化〉,《成大歷史學報》38期(2010),頁134、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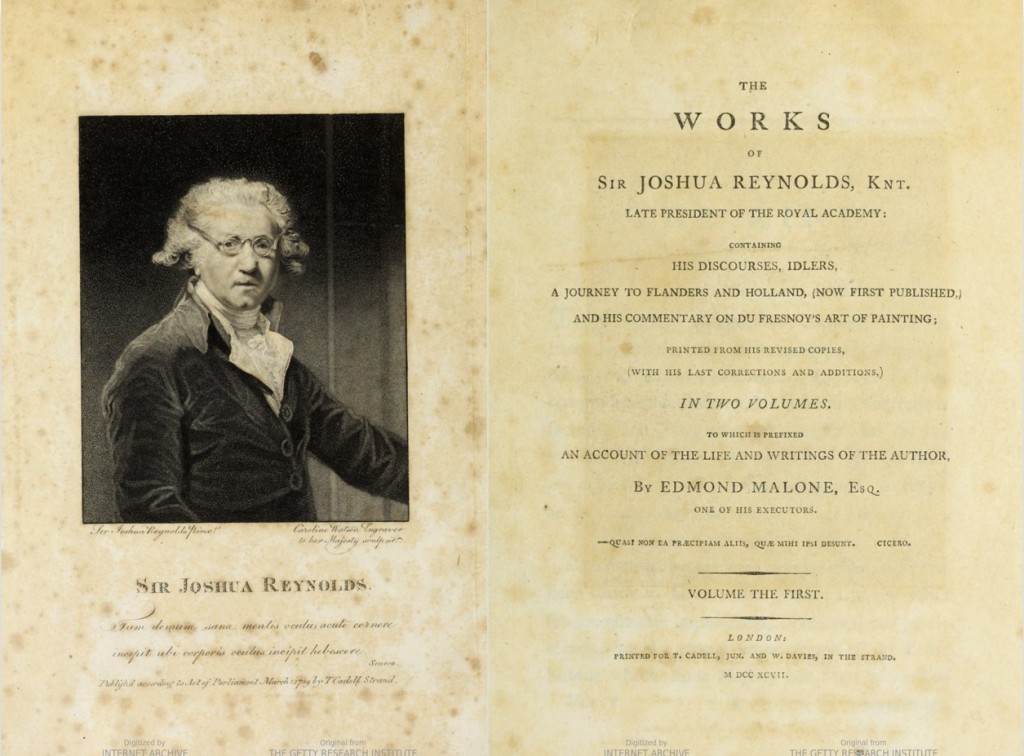
發表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