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切分une
自上世紀六零年代,西方藝術界發生了根本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普普藝術、觀念藝術、行為藝術紛紛興起,藝術家/作品和展示空間的關係也悄然改變。實際上,早在杜象把小便池放入美術館的那一天,就已經挑明了美術機構與文化定義權之間的關係,只是這種挑明尚只存在於藝術界內部。如同〈電影裡觀展,另眼試看〉提及,電影初發明的幾十年間,鮮少看到同期進入大眾生活的展覽被電影人框入攝像鏡頭,於此類似,六、七零年代載入電影史的經典作品中,「後現代/當代」藝術展覽的存在感也很低,反倒是能看到造型藝術之外的一些觀展場景出沒。
例如,克里斯.馬克(Chris Marker, 1921-2012)的先鋒短片《堤》(La jetée,1962),全片由黑白靜照串連而成,其中男主角接受實驗而記憶閃回的段落中,相當篇幅地展現了他與女子踱步於自然博物館的畫面。他們或俯身、或仰頭,仔細觀察著那些動物標本【圖1】,彷彿這是某種座標系,標定了存在過的證據,又像是對不可知未來的一種對照——那些已經死亡卻依然佇立在展示空間內的動物們,同樣注視著人類,暗暗預示著人類的結局。或許,相比藝術品這類被某些特定階層賦予「價值」的文化遺產,自然遺產的價值更加恆定穩固,也因此,導演將其作為時空凝結的象徵,在揉雜著戰後陰影的科幻主題情境下,更可能引發觀眾的深思。

同時代聞名於世的《遊戲時間》(Play Time,1967),雅克.塔蒂(Jacques Tati, 1907-1982)在巴黎郊區打造出巨型片場,一比一還原現代化的城市景觀。影片開場不久,便著墨於博覽會的趣味【圖2】——演員推開倒映出艾菲爾鐵塔的玻璃門,人們進入各色新奇產品的展示/推銷攤位:方便畫眼妝的可上翻鏡片女式眼鏡、帶有仿車燈設計的吸塵器、希臘柱造型垃圾桶等,參觀者/潛在消費者面對這些莫名其妙的玩意時,或驚嘆、或詫異⋯⋯。這番描寫既是塔蒂對當時都市生活變化的敏銳捕捉,也是對現代化社會出現「無用」設計的幽默調侃,更是對都市化科技進程的超前回應。電影裡,以形似商店櫥窗的場面調度,一一曝光摩登家庭們千篇一律的晚間生活(相似的客廳家居裝飾、播放著同一個頻道的電視機⋯⋯)。大銀幕前的觀眾既是旁觀者,也可能是這些同款生活的親歷者,不如說,這是導演從人類學或社會學的角度,進行另一層次的別樣「展示」,也是他對看似精緻便利,但缺乏原創趣味的現代生活的冷嘲熱諷。

話說回來,當我們提到「展覽」時,通常默認其指的是美術館/畫廊裡發生的文化藝術活動。隨著時代推移,劇情片裡的當代藝術展/作品又是如何呈現的呢?這是個頗有意思的問題。因為似乎直到千禧年後,我的腦海裡才陸續出現對當代藝術直接或間接的品評場面(當然也可能是我閱片不夠廣)。比如2011年叫好又叫座的法國電影《逆轉人生》(Intouchables)【圖3】裡,癱瘓的富人主角坐著輪椅,前往畫廊欣賞當代抽象畫,一擲千金買下後,遭黑人看護吐槽的橋段;再往前推十年,根據同名漫畫改編的美國獨立電影《幽靈世界》(Ghost World,2001)裡,桀驁不馴的「異類」少女主角,也在藝術課上直接回應了老師對於藝術的見解,卻落得尷尬下場。

而將「當代藝術展」作為絕對主角並以此展開多層次敘事的代表,非2017年的瑞典電影《抓狂美術館》(The Square)【圖4】莫屬:主人公設定為藝術博物館的館長、西方精英的代表,故事圍繞著展覽宣傳引發的一系列風波,猶如一面照妖鏡,牽扯出上流社會的虛偽、歐洲移民問題、階級隔閡等等議題。影片裡,展館策展團隊為如何「炒火」新展絞盡腦汁,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館內拒普通觀眾千里的白牆,和不明所以的裝置作品。同時,行為表演這一藝術形式也被導演格外關照,影片的小高潮便是晚宴上一眾衣冠楚楚的賓客,面對熱場節目裡「大猩猩」模仿者逐漸出格的行為演出,大驚失色,良久才意識到局面失控,表演和現實的結界被打破……(有關這部電影的評論已很多,也就不在這裡過多展開。)

雖然故事脈絡各不相同,卻不難發現電影創作者們不謀而合的默契——試圖扯下當代藝術的「國王新衣」,有時候還不忘藉此揶揄所謂的精英人士。其實,隨著六零年代觀念藝術的不斷壯大,看展覽早已不再只是欣賞靜態的一幅畫或一尊雕塑;普普藝術以降,對現成物/商品的挪用,也讓日常之物在藝術家和藝術空間的雙重「庇護」下,被賦予了額外的崇拜價值。顯然這讓人們與美術館藏品曾經抱持的態度和連結發生了改變,正如波里斯.葛羅伊斯(Boris Groys)在 《藝術力》中所寫:
「過去美術館的功能與今日一樣,是公共檔案的保存之處。只不過它所保存的是特殊之物。……傳統的美術館假設它收藏的藝術品擁有永恆的藝術價值,這些價值乃内含在藝術當中不隨時間改變,可以吸引與說服當今的觀眾。」[1]
「今日的美術館與其他的保存場所愈來愈相似,因為美術館所收藏的藝術文件,在公眾面前不見得是藝術。美術館裏的永久展示不再是(或至少不常是)一個穩定、永久的展出。取而代之的是美術館愈來愈成為暫時性展覽的場所。作為傳統美術館之特性的收藏與展覽的整體性,因而被破壞了。」[2]
引文提及的「傳統的美術館」裡「傳統」二字相當值得玩味。延伸到電影創作來講,「傳統」的導演更樂於把「美術館看展」和中產/富人階級、社會菁英直接綁定,作為敘事的一環,當然運用手段各有差異。諸如希區考克的懸疑故事裡,觀眾容易忽略主角的社會地位,而僅把這當作推進情節的一個插曲;到了2000年後偏社會議題的現實主義電影中,則逐漸將這一階層對藝術展(尤其是當代藝術)的熱情,作為諷刺的對象,演變為一種刻板印象。
我認為,藝術展/藝術空間在銀幕上以何種基調展示,亦會潛在地影響大眾對藝術的印象和態度。事實上,現實世界的展覽多種多樣,比如紐約MoMA早在上世紀三、四零年代就已有設計類的展覽。如若導演們一味地將「看展」作為有錢有閒階層的消遣活動,則會讓「觀展」本身具有的多面性在無形中被壓平,亦即成為某種單一的文化符號。
就我個人而言,或許較為理想的畫面,出現在日本導演濱口龍介(1978-)的《睡著也好醒來也罷》(寝ても覚めても,2018)裡:女主角走進一家公立美術館,是其喜歡的攝影師牛腸茂雄的作品展,觀展時她偶遇了一見鍾情的男主角⋯⋯。看似俗套的開場,卻有著極為平民化、隨意的鋪陳,無論男女主角,都是普通的「打工人」,但因為「看展」這件事觸發了交匯,形成了故事的開端。隨後,攝影展再次登場在一個街邊小藝廊,以肖像為主題的展覽海報下映射出劇中人物的兩張臉【圖5】,與整部影片的推進形成某種對位關係(結合攝影師的創作主旨,在此不多劇透)。導演對「看展覽」這一元素在當下時代的巧妙捕捉和再現,跳脫了慣常的敘述模式,彷彿是我們每個人都能涉足的日常,又暗藏了無窮的可能性與戲劇性。

我想,不論展示內容為何,「展覽」作為一種公眾可參與的、揉雜了個體與集體記憶的活動,顯然具備了文化和社會層面的象徵意義。如何在電影這一虛構的影像媒介裡,更加豐富地、高明地呈現「觀展」這一行為,而非只是將其簡化為一個文化符號,這也許值得我們再反思和探索。
[1] 波里斯.葛羅伊斯(Boris Groys)著, 郭昭蘭、劉文坤譯,〈多重作者〉,《藝術力》(Art Power)(台北:藝術家,2015),頁140-141。
[2] 同上,頁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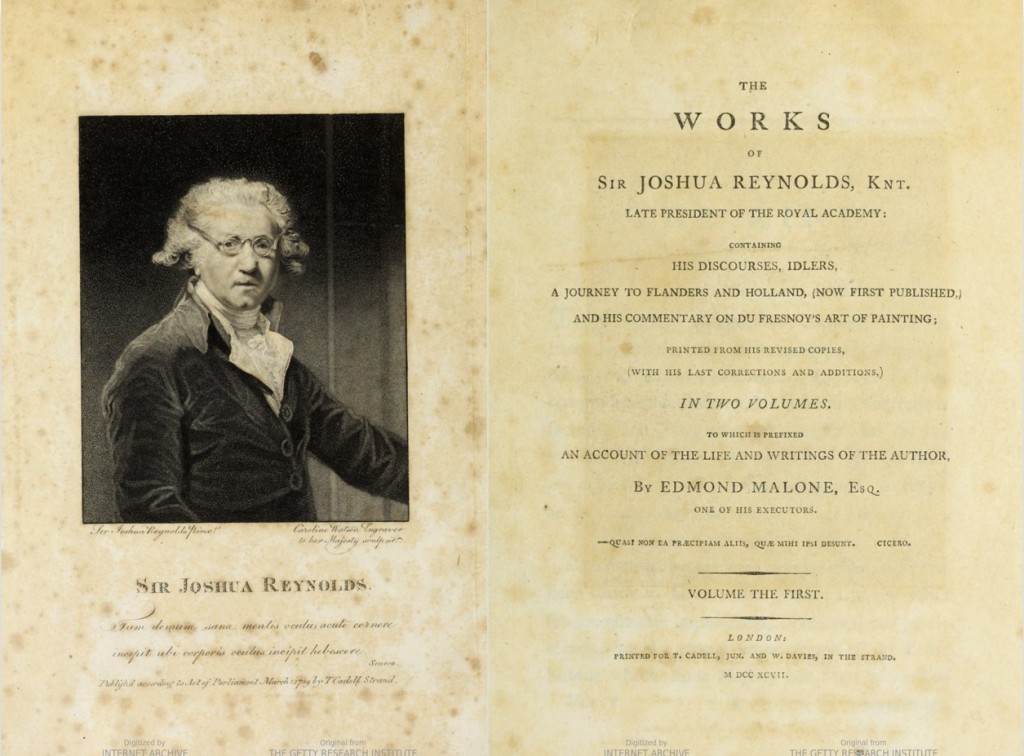
發表留言